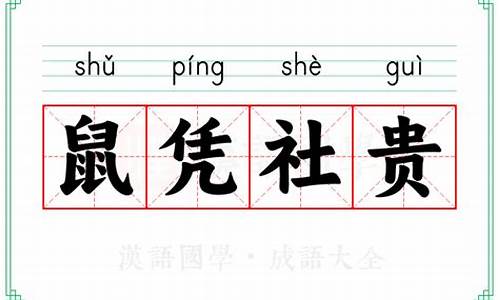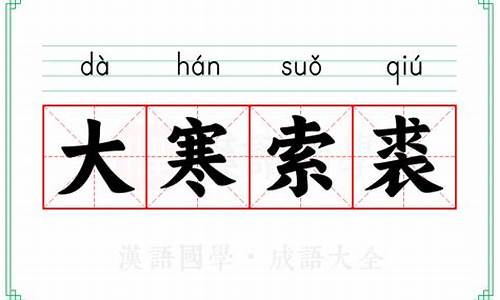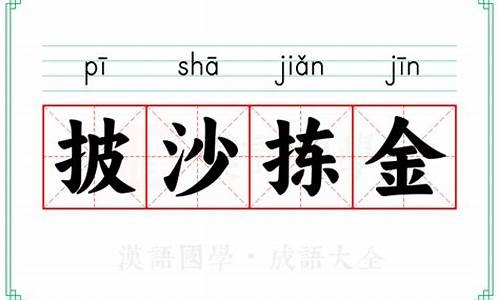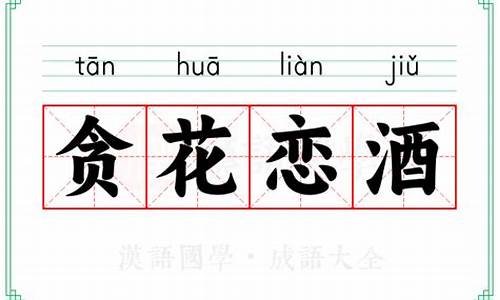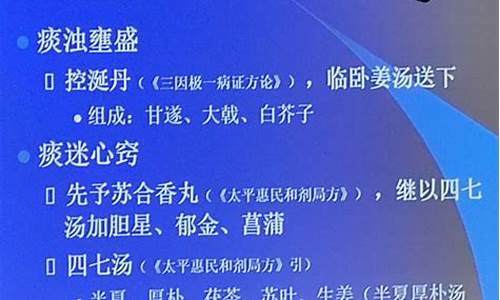轼顿首再拜闻足下翻译-轼顿首再拜
1.《答李端叔书》-二十四诗品读古文之自然
2.答李端叔书文言文阅读答案
3.答李端叔书的作品原文
《答李端叔书》-二十四诗品读古文之自然

好久没有写二十四诗品读古文系列了。也许是因为写二十四诗品需要比较好的一个静心状态吧。所以一直也没有动笔。而且,二十四诗品中我也已经写过了九个。共写了八个人的文章,其中也只有江文通是双响,不过也没有办法,以江淹的文采这也实至名归。但是这次选的文章却又是苏东坡的,又一个双响。当然从文学史和民间传说的口碑苏东坡的名气还要大于江淹江文通,本来我想选的是后赤壁赋,可是却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读到了这篇并不是很长的答李端叔书。这是一篇回复仰慕者安慰自己的信,但是却是出奇的平和隽永。相比于写景抒怀而陈情于山水之间的文章,也许这篇文字更能彰显出这个被千古传颂的文人的真境界吧。
还是老规矩,先从二十四诗品的自然篇开始解析吧,
何谓自然,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其实也就是我想说的自然。与苏东坡同时代的欧阳修对于自然的定义——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万物皆变,万变皆通这其中的道理就是自然。而二十四诗品之中描述自然的这四十八个字更是精彩迭出,情趣盎然。也就是这短短四十八个字尽得南华、道德二经的神韵。俯拾即是,不取诸邻。起句便是一派隐士风骨。仿佛一个安步当车的山中隐者在自己的山水之间顾盼自雄。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这四句话更是写得仙风道骨,步步莲花,举手成春的感觉实在是意境之妙法。而俱到适往更是一种雍容仪态。雍容仪态之中又能步步生莲,着手生春。这得是怎样的风流人物?真与不夺,强得易贫。也是尽得道德经之要旨。俗话说来便是:“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的境界。最后四句“幽人空山,过雨采苹。薄言情悟,悠悠天均”却又将这种飘逸空灵的隐士之感用状物写情的手笔描摹到了极致。幽人空山两句,意境好似戴望舒《雨巷》里的丁香花女子。最后薄言情语两句的总结,更是以极平常的悠悠天钧作为所有的自然感觉的概括。总而言之,二十四诗品里的自然,其实是一种极致的无欲无求的万物之美。
那么再回到我选的这篇文字。之前的二十四诗品读古文系列,或游记,或文赋,或幻想,或写实。只有这次选的《答李端叔书》一文是一封给陌生人的回信。那么东坡先生是如在给这个陌生人的回信里展现出自己自然地境界呢。先上原文吧。
答李端叔书
苏轼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犹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讠尧讠尧至,坐此得罪几,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已,何足为损益。
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
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李端叔的名气听起来似乎并不大,也不熟悉。如果我直接说他是重要的苏门文人。我想诸位看官也是一头雾水。不如我直接以文代人把他的名篇说一下。
这首词一出,大家马上就有了感性认识。原来李端叔就是写这首诗的人物。李之仪是名,端叔是字。按理说在宋词的诸多大家里,就凭这首千古传诵的卜算子,他也可算有一席之地的人物。而作为苏轼这篇回信的接受者。介绍一下李之仪似乎也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李之仪是沧州无棣(现在的山东庆云)人。精确的生卒年月都是学术界推论的一大课题之一,而且越来越像文字游戏。但是他的大概形象就是一个小苏轼十多岁的这么一个有些才华的仰慕者吧。李之仪中过进士。做过县令。还做过军中幕府,出使过朝鲜。而这样一个人物,却在登第三十年的宦海沉浮之后而从苏轼于定州幕府。而苏东坡对他的评价也甚高——工尺牍,入刀笔三味。所以李之仪的仕途高峰也很合理的被定格在枢密院编修的位子上。简单的打个比方,枢密院编修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厅的秘书,虽然位不高但是权不小。而李之仪巅峰时期(元丰三年1080到元丰八年1085)却正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时节。此时的苏轼惶惶如丧家之犬在黄州夹着尾巴做人。而李之仪却是已经实际上贵在中枢的枢密院编修,翰林知制诰。形成了二人实际上的悬殊地位。但是李之仪却异常努力的要去结交苏轼。按照答李端叔书此文的说法来看,苏轼应该是很早就收到了李之仪写来的书信(元丰三年)却一直没有回复。直到后来又收到第二封书信才做了这篇答李端叔书。
那么下面开始回到原文吧。
文章第一段充满了歉疚之意。是一段给李之仪的满满歉意的文字。
这一段的内容,在我们常人的书信往来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现在的社会已经逐步减少了纸质书信,而代之以电子邮件,但是这些尺牍信件中的礼仪还是我们传统人际交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而苏轼这一段就是比较典型的略带歉意的范文。顿首再拜和闻名已久都是虚礼。苏轼之前是否闻李之仪的名都是需要进一步考证的事情。但是不这么写也不符合传统。后面的以见所作诗文而足以仿佛为人云云,个人以为也是更进一步的客套话。如果不是李之仪多次修书,恐怕苏轼也未必有时间会去仿佛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后学小子的为人。所以前面两句都是程式化的客套言语,接下来的内容才是有营养的部分。
从寻常不通书问开始,苏轼开始讲自己回信的原委。
这一段的信息颇多,可以看出的是,李之仪至少给苏轼写过两次信。第一次是托苏轼的弟弟也就是子由(苏辙)带来的,根据时间推算这应该是元丰三年的事情。而这一年,正是李之仪“崭然在疚”的时间——疚的意思是居丧,潘岳的《寡妇赋》中就有“自仲秋而在疚兮,逾履霜以践冰”的说法。而李之仪的母亲在元丰二年(1079)年去世,宋人丁忧要至少两年以上。所以苏轼这句话中的歉疚之情也是显而易见——你在丧母居丧的忧愁之中还给我写来安慰的信件,而我却未能及时回信去安慰你的忧伤。所以当李之仪第二次的信又来的时候,苏轼形容自己面热汗下,也是非常贴切的形容自己惭愧的场面。
接下来的这一段俺觉得其实并不是太和谐,这段有点像是明星对于自己粉丝的一个撒娇的行为。而且这个撒娇的行为还颇有些傲娇的味道。翻译一下情绪就是:
“你怎么会喜欢我啊,我的行为经常不为大众所理解。你这么明白的人,怎么能像秦观和黄庭坚一样,说不清楚为啥就把我当明星追……
这个颇有点拒人千里之外的酸酸的欢迎词就这么被苏大诗人拍到了李编修脸上。这其中的欲拒还迎,欲说还休的意思真的是让俺有点尴尬症复发的意思。当然,换个角度理解,认为这是苏轼的隐性规劝也是有可能的。此时的苏轼还在乌台诗案的余波里苟延残喘;这么隐性的给自己的追随者提醒一下也很有必要。
总之,苏轼的这第一段,即表达了自己拖着始终没有回信的歉疚;又兼顾了传统的书信礼仪。同时还交代了事情的原委。顺便隐性的提醒了一下李之仪和自己交往的风险。这四个目的达到,有没有什么可能落在政敌手里的把柄,实在是技巧精纯。
第二段开始说自己。
这一段其实是极心酸之言。苏轼所分辩的也正是之前的乌台诗案的由头。苏轼也借故深挖了一下自己的思想根源。从自己为了科举读书开始,到了为了更进一步考了制策科的直言极谏科目。然后养成了一个喜欢诵说古今,考论是非的毛病。然后在实践过程中真的以为自己的嘴炮技能可以实际应用,结果差点被弄。这个其中“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一句放在这里实在是辛酸之至。但是单独拿出来,却又足可以为千古嘴炮的写照。
这一句说的颇有些委屈。翻译一下情绪就是——我不过是说说而已,又没有真的做。这都是俺一路科举的职业病。就像自鸣自赏的鸟叫一样,与世事无关。
这样的说法,可以认为是大诗人在乌台诗案受挫之后的口不对心的反省。这等例子,翻翻双百方针之后的过关检查便可知文人心计——当把嘴打的稀烂的时候,自然可以听到自己想听的东西。所以说这第二段虽然是说自己的自况言语,却是颇有些口不对心的委屈和苦楚。说给李之仪听也算是苏轼的一种近似于亲近表示的倾吐吧。
第三段内容是此文之眼。明白第三段便算是大体明白了苏轼的乌台诗案后的下半生。
虽然还是谦辞,但是却已经有些颓唐的退意。由此可以显示,乌台诗案之后的苏东坡是真的怕了,开始颇有悔意的对待自己之前的偌大文名。
这两句,便是此文之眼。着草履扁舟,放浪山水,杂处渔樵;这一系列行为都是表象。表象之内驱动的心理因素是“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这一句道尽千古失意者的终极心态。
失意之时,纵情山水也好,渔樵耕读也罢;关键还是要自我隔绝式的断开与原有的圈子之间的关联。就连写得出前后赤壁赋的号称通达千古的苏轼也不外如是。很多人说这是自我保护的手段,但是从这篇书信看来,行文至此,似乎伪装已经渐渐剥去;这一段多少算是开始流露真性情了。所以自喜渐不为人所识也应该确实是苏轼的心境。
乌台诗案的迫害自然让苏轼心悸,但是这乌台诗案的起源也确实让苏轼更加后怕;而且,我很怀疑苏轼这个时候的心态还应该是很有些歉疚的。因为在御史台被李定、何正臣等人的刑讯逼问,大约他也不得不被迫跟着李定罗织罪名的方向咬出了一些干系人。所以此时的苏轼,既怕且愧。宁肯躲在醉汉百姓之中,也不想回答亲友书信吧。文人的独特属性在此一览无余。拿后世的理解来说,这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对待斗争的软弱性。这也就是北宋,要是放在大明,恐怕在东林党与阉党之间这样的文人还更多些。
所以再把话说开些,苏轼的诗都是文人的豪放气质,热血情怀备至而沉郁顿挫不足,大约也是此类道理。与稼轩武人杀伐,百战归来的武人性情迥异。但是人到中年,读起苏轼却真的是心有戚戚。少年时读《和子由渑池怀旧》还觉得阴沉消极,晦涩拗口,而今读来却是人景具备,情义悉符。
前面的那段文眼说的太过直白。这后面一句再往回找补一下。苏轼所谓的木瘿,石晕和犀通都是看起来似乎是有些病态却都被文人雅士所激赏的玩意儿。古之瘿木一般指的是贵重的楠木,楠木瘿中多有山川花木之文。同理,有晕彩的石头大多也会被作为宝石;就更不用说被视为灵犀象征的犀角上的贯通纹路了。而这些东西,都是如我之前被人重视的原因一样;其实都是我自身的毛病。潜台词就是,我以后得把我这些耀眼的才华收敛起来,别让大家再晃眼了。这样也比较容易和光同尘、泯然众人。
最后一段就更是阐明了今后的行事规划。
之前的那些晃人眼目的名气和文采都是病,得治。这些苏轼在黄州谪居已经想清楚了。
我原来的形象很快就要改变了,你还追星吗?也就是说,你美滋滋的想要结交的故我已经被我决心要构建的今我所替代。
你也别被我的这个变化所误导了,否则闻声而不知情,慕华而不喜实。你不见到我我也不知道你喜欢的是啥。这段话看起来像绕口令,其实却是苏轼与李之间确认眼神的一种仪式。苏轼的意思是你之前仰慕的如果是我的虚名和表象,那么相见可能能就会失望。但是也只有相见才能说清楚。说个题外话,这个到很有点像因为文字结识的笔友之间的关系吧。
这个结尾却也还是往回找补的。明确说了——这篇尺牍信函不算是俺的文章。只是信笔写来的。不免多写了点儿而已。你也别给别人看云云。然后就是些礼节性的问候与嘱咐。
再回过头来统合起来看。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苏东坡黄州心态的一个写照。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名满天下。甚至被宋仁宗认为是天赐给自己儿子的现成宰辅。然而与王安石新政政见不合的苏轼却并没有显达,只是颇有文名和清名。
从徐州改任湖州的一封谢表之后,却被天塌地陷般的墙倒众人推。除了自己被锁拿回御史台审问,连自己之前的文字都拿来细细检索,并将文字往来的人物逐一讯问。在自己的文字之中寻章摘句的吹毛求疵,然后上纲上线罗织大罪。靠着太后垂悯勉强逃得性命,谪居黄州。
而谪居黄州之后,便开始避隐朝事,纵情山水,努力向佛道求证内心自然。这个便是我选了二十四诗品中的自然部分来暗合之的缘故。苏轼的这篇文字却也正式表露出因此抛却了之前写策论而来的嘴炮秉性的意思,开始从渔樵耕猎的百姓之间寻求自己的心灵寄托。
以“俯拾即是,不取诸邻“的方式明白了”真与不夺,强得易贫“的道理。苏轼的东坡之号也正是因为在黄州期间因为经济状况下滑,而要了一片黄州城东的荒废坡地。作为自己的田地垦荒耕种来贴补家用。
所以说苏轼此时的隐和陶渊明当年的隐还有所不同。之前写的归去来兮辞,陶潜归隐的由头是彻底的失望乃至绝望。而苏东坡呢,却是在黄州开始痛定思痛的反省自己前三十年的所为。答李端叔书的文章要旨似乎也正在于此。牢骚也有,委屈也有;但是想想自己也确实是有些问题和处理不当的地方。所以先从自己做起,且不理会亲朋故旧劝慰,努力的让自己充实起来。以一种站在大地上的踏实感觉更自然的仰望星空。这个也许才是大诗人的高妙所在吧。同时也是这篇回友人信的重点。
当然更有意思的是,李之仪自己的《姑溪居士集》中并没有收录他写给苏轼的书信。作为一个苏轼的迷弟,疏忽不录不太可能。只能是有意不录。而有意不录的原因似乎也很明了了,首先是可能李的来信之中颇有些议论诗案或者朝廷的言语,其次便是李之仪自己接了苏轼的回信之后也明白了在黄州的偶像并未彻底消沉,而是反躬自省的开始了自然的新生;这些也感染了李觉得自己的劝慰显得无足轻重了吧。
最后,虽然我颇喜近体诗,同时也对围城之中董斜川的“陵谷山原”之说不屑。但是对于苏东坡的近体诗态度还是颇有一致的。至少在宋诗之中,东坡先生的近体诗没有太出色的。哪怕是我激赏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是中上之作而已吧。这篇文字也已经是二十四诗品读古文系列的第十篇了,算是个整数,所以凑一首七律做结吧,
失意何妨隐庶黎,此心直到夜郎西。
由缰信马官途短,野渡横舟鵩鸟低。
赤壁赋中知宿命,黄州城外履畛畦。
今朝风日莫搔首,耕罢东坡草素题。
答李端叔书文言文阅读答案
1. 苏轼的《答李端叔书》全文翻译
闻足下名久矣。③昌歜,回首我这三十年来的所作所为?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先捎来先生的书信。被贬以来。其实何所有; 我被别人憎恨,待遇益隆,去考什么制策,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妄论利害; ,可是等到您卧病在床了" target="_blank">,谗说得失,我努力地封闭自己?
 ,这特别不是我期望的,不敢作文字。(我)听说足下的名字很久了; ,自鸣自已?shareid=1824720879&uk=3590486522" name="答李端叔书,不觉累幅,不应该轻易赞许一个人,虽然见的还不算多。
 ,就不敢再轻易提笔作文。又称昌菹,览之面热汗下也; ,可是您始终不抛弃我,(这就不可饶恕了),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自幸庶几免矣; 得罪以来,我已经得到了这个官,可是如果把他们的口味强加为众人的口味、羊枣,以取妍于人,无一字见及,递②中再辱手书,(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很高兴自己渐渐不被人认识了。此书虽非文,如人嗜昌歜③
答李端叔书
苏轼
原文
轼顿首再拜。譬如候鸟时虫自鸣自唱:驿站传递?这件事不当面讲不能尽言其详。倒是我弟弟子由来,亦不能以一字奉慰,真以为然耶。谪居无事。
注①斩然在疚,而二子独喜见誉,又复懒不即答.cn/geren/wzck/201303/233262,不过专门为了应对科举罢了,常常被路上碰见的醉汉推搡诟骂; 。
 ,现在十分寒冷.oldq、秦观这些人的话。如果认为这两个人的口味不对:; 。
 。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我对您的)怠慢之罪还可以宽恕,石头上有晕斑,有书与之亦不答、秦太虚辈语,愈非其实,但信笔写来也已不知不觉累积成篇。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皆故我,您真以为是这样吗,而足下终不弃绝,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寒苦,默自观省,犀有通; ,竟到了这个地步。常常穿着草鞋,贪得不已。平常没有书信往来问候,非今我也。
 。
 :
2. 苏轼的《答李端叔书》全文翻译翻译: 我向您致敬。
听到您的名字已很久了,又在熟识的朋友那里常常见到您所写的诗文,虽然不多,也足可以大体知道您的为人了。 平常我们之间不通书信,怠慢的过错还可以宽恕;等到您痛苦地居丧,我也不曾写一个字来慰问;鄙人的弟弟子由来到这里,先承蒙您赐我书信,又一次因懒惰而没有立即回信。
笨拙迟钝,不讲礼貌,到了这种程度,而您却到底没有弃绝我。近来在驿递之书信中又收到您的亲笔信,对我如此情深义重,我读后真要脸上发烧惭愧而汗下了。
我年轻时读书写文章,只是专门为了参加科举考试罢了。等到中了进士以后,还贪心不足,又参加了制策的专科考试。
其实有什么实际意义? 而那次专科考试号称为“直言极谏”,所以常常谈今说古,考证评论是非,以求得符合“直言极谏”的名称罢了。人苦于没有自知之明,既然因为在这个名目下考中了,便认为确实在这方面有点才能,所以在文章中争辩、谈论,直到现在,因此而得罪差一点被处,真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多么可笑啊。
然而世上一般人便认为我要想标新立异,那就太过分了。胡乱地论述利害,评说得失,这正是参加制科考试的人的一种习气,好比候鸟和时虫,到时就叫,过时就停,对于当前的政治又有什么损害呢?我常常怪如今的人太过看重我,而您也这样地称扬我,更加不符合实际。
原文: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髣髴其为人矣。
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
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几,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 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
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
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出处:出自北宋苏轼的《答李端叔书》。
扩展资料:
当时在朝为官的李之仪为苏轼鸣不平,积极联系好友和官宦在朝中活动,以求让苏轼早日返京,并寄书信表示慰问和思念。《答李端叔书》就是苏轼的回信。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善用比喻说明道理。谈到人们对自己的看法时,苏轼以“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作比,说明人各有所好,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不可能众口如一。
苏轼还以“候鸟时虫,自鸣自已,何足为损害”作比,说明正制科人论说利害得失,就像春燕秋虫一样,该叫的时候就叫,过了季节就不叫了,对于他人,既无补益,也无损害,而由此引来杀身之祸, 既可悲,又可笑。
3. 《答李端叔书》的翻译在下顿首再拜。久仰大名,我曾拜读足下诗文,虽所见不多,也足以评断您之为人了。自惭平日书信往来甚少,公患病之时也未书只言片语送抵床前,倒是我弟子由先捎来先生书信,既便如此我还犯懒没有回复,实在是礼数不周,万望海涵。在下对公如此,而您却再次来信询问,待我之厚,令我无地自容啊。
愚以为:先生才高识明,不宜轻出赞许之言,莫非您觉得黄庭坚、秦观之才,真如人所盛誉的那样吗?不肖之人为人所憎,而此二人爱听溢美之辞,正所谓昌歜羊枣,陶醉其中,但二人对所得赞誉之思辨恐怕就少之又少了。
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我年少时研习文章经略,不过为应对科举罢了,而在进士及第之后,又贪得无厌,去考什么制策,制策意在选拔直言极谏之臣,故后来每每评论是非,纵论古今,在下所言都只不过是为应和这个科名而已,做人苦于没有自知之明,我之所以得以为官,不过是考场得意,并无实学,而我却自以为有什么经邦纬世之才,实在可发一笑,遇不可耐啊。看看今日,竟为阶下囚,险些获罪而,这不正应了“齐人以口舌得官”的笑话吗?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空谈国家社稷、利害得失,这正是制科人的不良习气。他们的言辞啊,都是说给自己听的一样,孤芳自赏,不切实际,如同候鸟时虫自鸣自唱,哪里提得上什么利害于社稷民福。我每怪人们对我过苛时,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
获罪以来,活动范围就只局限于谪所境内了,常常穿着草鞋,驾着一叶扁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与乡野的樵夫渔民一起起居,有时还会被路上碰见的醉汉推搡诟骂。虽然如此,但我心中不由自喜,此处既无人识我,也就不必担心言语有失,而遭构陷了,唉,倒也自在。平生亲友,知我遭贬外放,也不再与我联系,即便我写信予之也不见一封回复,大多还在暗自庆幸未受我连累而遭一劫。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奇树之有木瘤,怪石之有褶皱,犀角之有洞腔,本都是事物病态表征,可它们却凭此病态深得世人的欢心。
被贬以来,无事可做,终日深自反省,回首我这三十余载的“有所作为”正是这般取悦于人的病态啊。先生对我的印象恐怕都是昨日之我,并非今日之我也。这不是重相而轻本吗?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有些话一定要当面才可尽言其祥啊。
某以文章获罪,所以出狱之后,不敢再轻易提笔作文,这封回信虽算不得什么文章,但信笔写来也已不觉成篇,先生还是不要给别人看了吧。小心为上。
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4. 求《答李端叔书》苏轼 全文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
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
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屡,放浪山水问,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荆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答李端叔书的作品原文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独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 足下才高识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 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歜、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 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直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 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
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