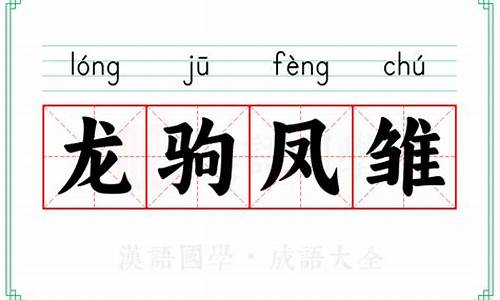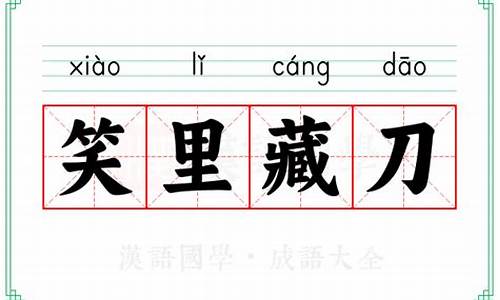掉书袋是哪里话-什么意思啊
1.关系不错的朋友说话老是让人不舒服怎么办
2.请解释:古代诗歌的“性灵说”
3.古人谈:寻常话语中引经据典
关系不错的朋友说话老是让人不舒服怎么办

可能你这个朋友文化水平、文学修养较高吧。如果不是故意掉书包的,而是他/她平时的文化素养导致,你也不用太介意。有这样的朋友,还可以提高自己的水平呢,是件好事啊。如果是故意体现自己而令人难堪的,可以考虑适当的保持距离。
请解释:古代诗歌的“性灵说”
要目:清袁枚论诗时提倡“性灵说”,意即自由抒写,不拘格套,要求真实反应性情,主张个性解放。这与公安派的主张相似。还主张反道学、反传统、反复古,反对雷同因袭,强调诗歌的独创性体现个性。因此其诗歌创作大都直抒胸臆,语言通俗,与白居易有些接近,具有洒脱、通俗的特色。
细述:性灵说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答施兰□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是不能泥古,要以自己性灵为基本出发点:“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古人谈:寻常话语中引经据典
过去上高中,讲到辛弃疾词两首《水龙吟》和《永遇乐》时,语文老师提到过辛的毛病就是。这样的评价其实也是历来的评价,如《历代词话》评“放翁、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要是一癖”,《古今词话》也说“陆辛时时”。
如今我们寻常时候倒不觉得严重,可见古今差异,此处不妨举出几个古时令人失笑或讥讽的例子来聊一聊。
话说北宋有个名将叫党进,他不怎么识字儿,一次被派往边地防范秋高马肥时北人南下,辞别时入朝致词,太祖知道党进不识字,让人告诉他不必来了直接走吧,党进脾气倔还不肯,司职上朝时班列礼仪的官吏在笏板上写好了词儿,嘱咐党进背熟咯。
然后上朝致词,党进跪在那儿一言不发。突然抬头来了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搞得大家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左右问他为啥突然说这个,党进说那些穷措大 (贫穷的读书人) 老是,我也来两句让圣上知道我也有读书。
“朕闻上古,其风朴略”出于《石台孝经序》开篇,为唐玄宗时整理《孝经》的各种注疏之作。但此处可见,这句话说的毫无关系,基本属于莫名其妙,所以左右才会问他为啥说这个, 这算是非常纯粹没有上下文、单纯想说点儿啥的那种。
其实说起,很多人应该还会想到张岱《陶庵梦忆》卷五中范长白关于“少焉”的故事。
这里主人提到的乡里缙绅以“少焉”指代月亮,就是 典型的不自然引经据典而 断古人文章以取其义、却不具备通用性使人理解的 。笔者猜这位缙绅或许还不会句读,把“少焉”和“月出于东山之上”连起来,以为是“少焉月”,就如此指代了。这样引申实际是扭曲原意而用的。
但这与常说的“指代”不同,指代没有扭曲字词意思,反而是贴合原意并获得了广泛认可的。不过也有不扭曲意思,但仍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如小说《品花宝鉴》中王恂的两个内舅,孙家嗣徽、嗣元两个儿子。第二回《魏聘才途中夸遇美,王桂保席上乱飞花》里第一次介绍两兄弟都是文理欠通,经文读的不多却酷爱,苏州拔贡生高品给兄嗣徽起外号叫“虫蛀千字文”,弟嗣元口吃又说不清,外号叫做“叠韵双声谱”,“这两个废物真是一对”。文中两兄弟来见王恂又碰到仲清:
读来让人捧腹,可笑处都已加粗,今人有时就喜欢类似的运用敬称、典故和成语。而可笑之处就在于一是 不知原意而乱用经典 ,如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一句被用来说人“如”鸟。二是 不辨作者,或者其他借代和人物字号等 ,孙嗣徽误听为秦某,可见不知靖节先生即陶渊明。三是 在寻常口语中乱用敬称、自谦和成语 ,只放上面或许对比不出,以下为该书中第六回里,大年初六姑苏会馆团拜时的对话:
如此可见寻常话语就用口语说即可,如孙家兄弟敬称成语随口用,一句话塞进四五个,除了屁用不顶。
再引一处第八回文末郑聘才和李元茂因为被扒了银子没法儿付给相公和饭馆儿钱,而找孙嗣徽借钱而嗣徽就说出了以下的话:
如此可见连篇累牍地引用经书典籍替代原本可以随意表达的话,不仅不会显得自己读书多,反而会为人所耻笑,因为 这种单纯的替代很明显的表明了表达者没有充分理解经书典籍的含义和融会贯通方式、却又急于表现的状态 。 而这还通常伴随着撇弃通俗用法而专门寻找生僻用法。
如《柳南随笔》中说:
那再看一下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是如何的:
其实主要是下半阙中一句都有一两句用典,如此频繁确实对于古人来说算是了,今人多不会主动意识到主要是因为辛用典适于表达自身感情而没有过多偏离原意,前后衔接是存在因果的,不像前文孙氏兄弟天上一句地上一句。
所以可见,只要符合原意运用且不是很频繁,或者即使不合原意但适当发散也可。除非是本来就为了博人一笑,则随意解读以达到搞笑结果即可,比如1932年出版的《唐祝文周四杰传》中第二十二回有:
文中祝枝山拿唐伯虎“满足”家中八妇的事与华太师打趣,便是刻意生硬解读以达到效果的例子,如此用的好便是幽默,令人捧腹且无伤大雅。
此外“”也可以表现得有水平,那首先就不能太密集,其次慎重使用敬称谦称和成语等,最后就是 必须结合上下语境选择契合目前交流内容的词句 。妥善地是可以彰显的,比如《夜航船》中卷五伦类部里的奴婢一篇中的读书婢,记郑玄家婢女:
同一件事也可见于短篇小说集《西湖二集》中:
如此则也是可以的,只要应该注意的毛病一定注意,否则容易不成,反被人耻笑。但其实也可以见出多读书的重要性,读的少了难免反复引用,如果同时理解又不够多只只看字面意思,甚至不顾字面意思,则必然容易出丑了。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